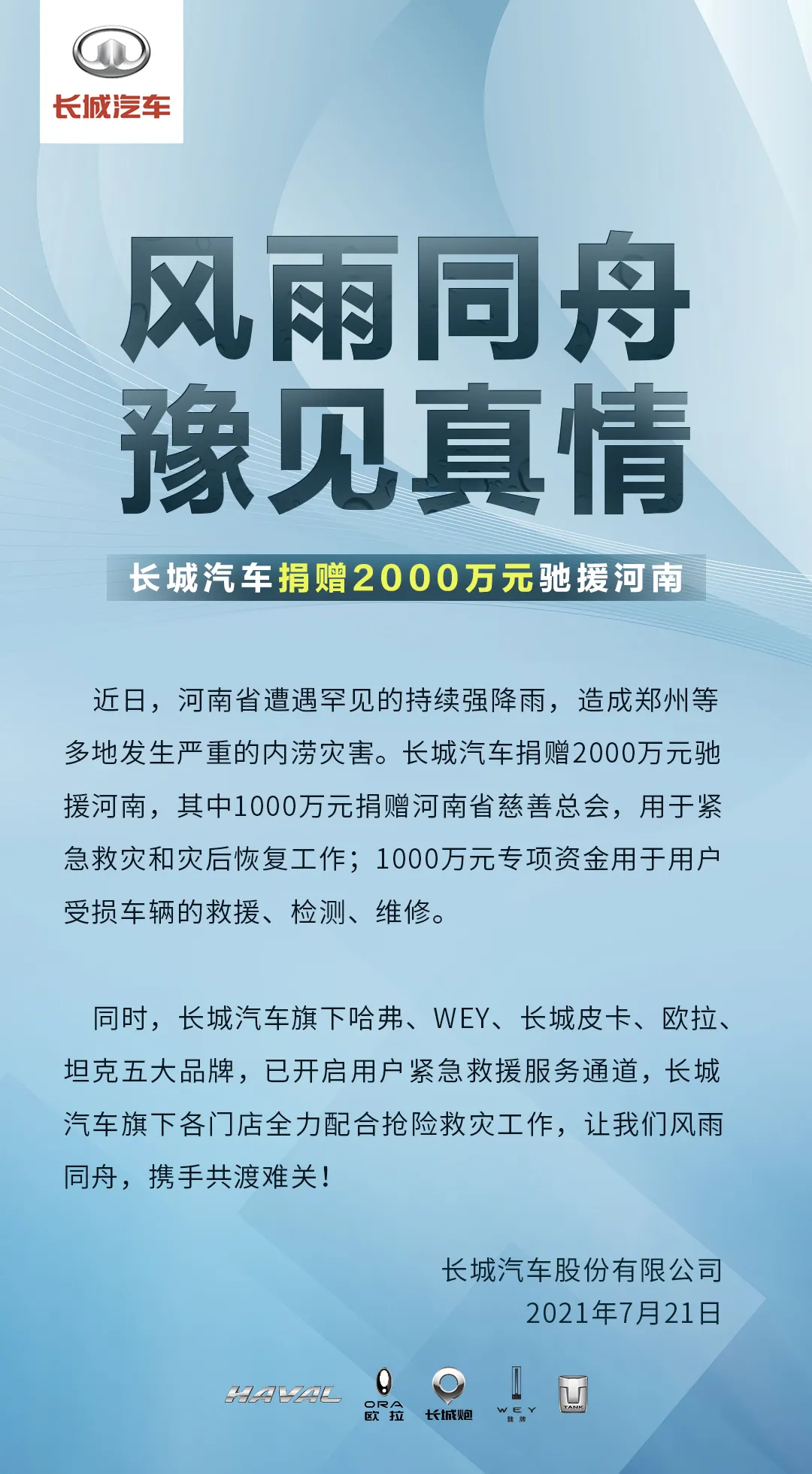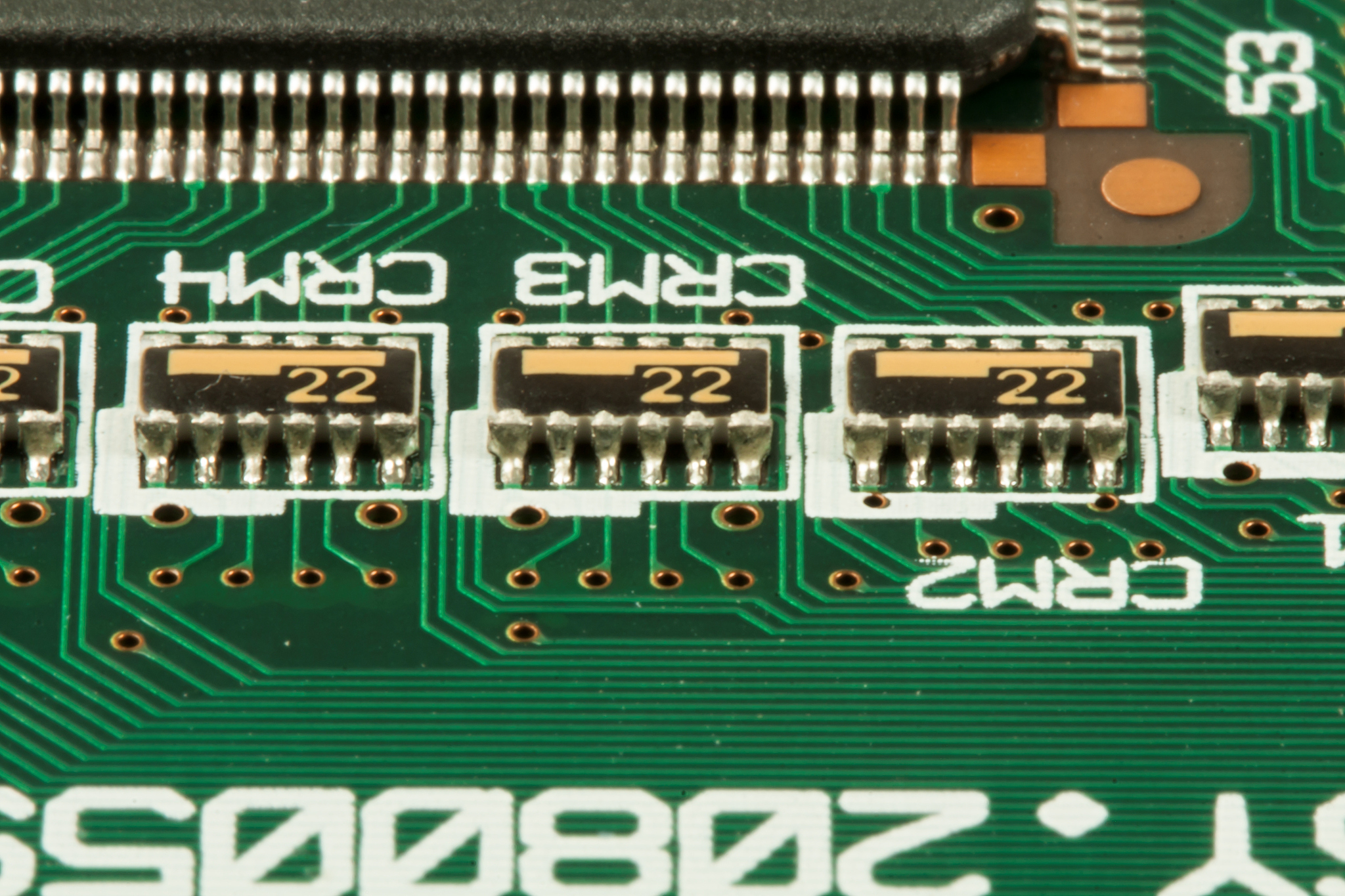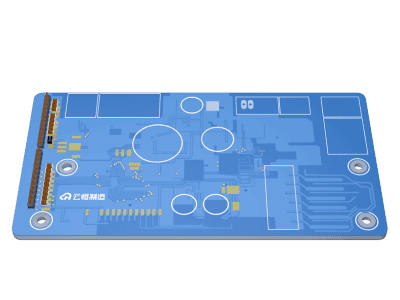游戏和玩是一回事吗?(游戏和玩是一样的性质吗)
玩与游戏
首先让我们从木马讲起,或者,只是一根被孩童当做“木马”的棍子说起 。
当这根木棍被丢在地上的时候,它就仅仅是一根木棍,而当木棍被一位小男孩捡起,当做玩具、亦或是“马”的时候。
首先,这位小男孩并非单纯无意义地“玩弄”木棍,所以与其说“他在玩木棍”,不如我们也可以说,他与木棍一同游戏,或,他与被他当做“马”的木棍一同游戏,只是或许他时而以这样的方式玩,而时而以那样的方式玩,他的游戏没有固定的规则,规则只是他自己随时制定的,为的只是能够在游戏中享受着骑马的乐趣。而此木棍作为提供乐趣之物,与他共同打开了一个游戏世界。
为游戏做定义的事情已经有人干了不少,但是就连维特根斯坦都只能将其归于“亲缘相似”,甚至有人认为游戏/玩需要分别定义。[例如The Rules of Play]
在此意义上,我认为首先游戏(game)与玩(play或作为动词的游戏)不应区分,亦或者它们共同指向了这种运作的过程。
如果我说,“装作骑马的样子”是一个游戏,或许有些人要反驳,因为这样的过程似乎不足以成为一个游戏,其中漫无目的地无规则性,不足能构成一个如同足球比赛式的,有着严苛结构的游戏。
但是我们不妨说,他只是在玩一个规则性不那么强的游戏,亦或者他在玩的时候不断地,有意识无意识地修改着规则。
实际上我们日常指称游戏的时候,皆是模糊的,游戏与玩,只是我们描述时强行分开的动词与名词,是语言局限的结果。
我们试图用名词“游戏”指的,并不是那“54张牌”的物作为游戏,也不是某一个玩具作为游戏,实际上也不能是某一个电脑里的软件,也不是某张电脑游戏光碟的物,也不是指具体的“规则”本身;而我们也不能用“玩”来指小男孩与木棍的游戏,我们只能描述一个状态,他在玩。
不妨尝试感受下,当我们用“游戏”——作为名词时,我们似乎将游戏看做一个稳固的结构、一个存在的静态对象物,但此时,其中“玩家作为参与者”的那部分就被遮蔽了;而当我们只说“玩”作为动词时,玩家出现,但似乎只勾勒出了一个态度,我们并不知道他在玩小提琴(的游戏)还是在玩《魔兽世界》,“他在玩什么?(对象)”亦或者,“他如何玩?(方式)”,这两者都茫然不清。
很多时候,当我们说“我们在玩”,实际上就已经包括了“我们在玩游戏”这样的意思。 “玩游戏”这样的用法是同义反复。“你们在玩什么?”的回答不会是“我们在玩游戏”, 而会是我们在玩“什么”,我们“怎样”玩?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怎样的?等等。
故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游戏,是指我们对待某事物(可以是自己/身体/思维)的某种运作方式,或我们期待的、正在进行的、之前进行着的运作方式。而在我们的情景里,小男孩作为游戏者(player),正进行如此的运作。
语言学考察
赫伊津哈有⼗分详尽的语⾔学考察,就像他也将⾳乐归⼊游戏的范围。也就像我们日常使用play从而去作为动词接上足球、篮球、乐器等。
希腊⼈表达⼉童游戏的⽅式是在词尾加-inda,是词缀⽽ 给⼀些单词添上“玩”的意思。
⽽παιδά-paidia,其词源意味“⼉童的或与⼉童有关的”,其派⽣词παίξειν(游戏)、 παῖγμα和παίγιον(玩具),可以⽤来表示各种游戏,甚⾄是柏拉图《法律篇》最⾼等最神圣的游戏,整组词 似乎都带有轻松愉悦,快乐舒畅的味道。
和παιδά想⽐,另外表示游戏的词άδὔρω ἄδνρμα则远⾮那么常⽤, 它略含“微不⾜道”、“徒劳⽆益”的意思” (赫伊津哈《游戏的⼈》第34⻚)。
真正让游戏成为游戏的
“游戏的严肃性”,是游戏这样亦庄亦谐的态度,游戏以缺席地方式在场。
是我们知道其并不“必要”,但是我们却投入其中。
日后再展开吧,问题已经回答完了。
2018.4.3